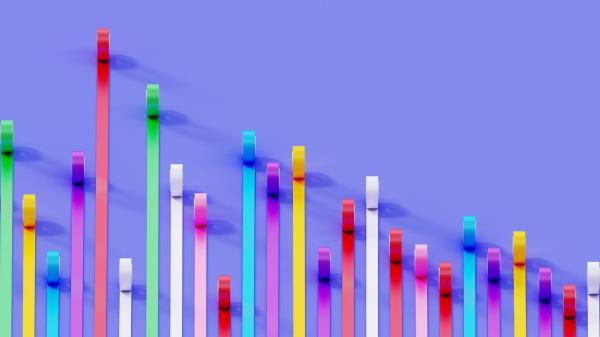几周前的一个周五晚上,快11:30的时候,我决定暂停写论文,休息一下。我煮了一杯土耳其咖啡,让它独特的香气弥漫在房间里,一边听着酷玩乐队的《满天繁星》,一边从打开的窗户望向天空。
在加沙,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阳光明媚,很少下雨,这与我的出生地爱尔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爱尔兰,我允许自己享受被一些简单的事情打扰的奢侈,比如早晨海鸥的叫声或无尽的灰色天空。
回到加沙,让我心烦的从来不是天气,而是以色列无情的轰炸、以色列无人侦察机持续不断的嗡嗡声,以及18年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令人窒息的围困,这些影响了我生命中的每一刻。
我猛地回到现实中,想起我必须给我的教授发邮件,汇报我的论文进展。打开笔记本电脑,我看到一条来自我关注的加沙新闻频道的WhatsApp通知,打破了宁静。突发新闻,加沙地带中部的布瑞吉难民营发生爆炸,目标是阿尔萨姆马克一家。
我失去了理智,因为在我们的房子被炸毁后,我的家人在那里避难。恐慌攫住了我。我一边颤抖一边给妈妈打电话。不回答。我试了一次又一次。什么都没有。我的心怦怦直跳,几乎无法呼吸。最坏的情况占据了我的脑海。我感到完全无力。
“在废墟下”
在尝试了几十次之后,我的嫂子达利娅用颤抖的声音回答说:“这是你叔叔的房子。我们没事,但你所有的表亲都在屋里。他们现在在废墟下。邻居们正在用手挖,把他们救出来。”
我叔叔的妻子苏阿德(Suad)今年55岁,从废墟中被救了出来,但她已经走了——她的身体没有生命。她当了二十多年的寡妇。她爱我的叔叔阿里,爱到不能再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的地步,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她的三个儿子,分别是17岁、20岁和22岁。
艾哈迈德的姨妈苏阿德在空袭中丧生。艾哈迈德Alsammak
苏德和我是亲密的朋友。她就像大家的第二个妈妈。去年9月,在我去爱尔兰攻读硕士学位之前,她开玩笑说:“即使你爱上了一个爱尔兰女孩,也要确保在加沙举行你的婚礼。”我想在这里和你一起庆祝,因为爱尔兰的天气很冷,我很容易得流感。”
接着,达利亚又发来一条消息,说我的三个堂兄弟被拉了出来,但受了重伤,其中一个被完全烧伤了。其中两人此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如果他们活下来并离开医院,他们将成为无家可归和受伤的孤儿,住在帐篷里。
几乎无法生存
在加沙,你很快就会明白,生存是一场日常的赌博,有时幸存者会后悔自己没有活下来。
突然间,我感到了这一切的沉重——种族灭绝的残酷。它只需要几秒钟就会被以色列的袭击永远粉碎。只有秒。
天空布满了乌云,开始下雨,但现在已经太远了,打扰不了我。我又给妈妈打了电话。她说,他们正在考虑搬到另一个地方,但由于天空中到处都是战机,他们害怕搬家。
就在八天前,我的另一个叔叔阿齐兹和他的朋友去附近的一个农场采橄榄。因为他们直到晚上才回来,他的儿子们一直在找他们。他们发现他的朋友被烧死了,而我叔叔的自行车和电话都沾上了血迹。
我哥哥告诉我,我叔叔的朋友的家人感谢上帝,因为他们找到了尸体,因为有很多流浪狗被记录下来,尤其是在加沙地带靠近以色列基地的地区,在废墟下吃尸体。
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已经禁止卫生用品、水、燃料、食品、药品和无数基本物资进入加沙,除了偶尔有几辆卡车。因此,疾病,特别是小儿麻痹症、皮肤病和肝炎在加沙地带蔓延。
联合国发言人上个月表示:“我看到的大多数加沙儿童都患有皮肤病和皮疹,他们生活在不人道的环境中,导致这些疾病继续传播。”
使加沙局势恶化的是以色列故意轰炸加沙的基础设施,使许多街道和流离失所者在帐篷里避难的地区充斥着污水。
观点:以色列禁止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及其运作将使加沙局势更具灾难性。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做什么?为什么它被视为巴勒斯坦人的生命线?
疾病
我的弟弟莫门今年24岁,是一名人道主义工作者。他两个星期前感染了甲型肝炎。他的症状很严重。然而,医生告诉他,由于以色列关闭了所有加沙过境点,没有疫苗,没有适当的治疗,只有止痛药。
由于卫生纸在加沙既稀缺又昂贵,就像无数加沙人一样,我的家人最近不得不多次使用旧衣服和织物来代替!
“我还是腹泻,但你的旧衣服真是救星!”黑暗时代的兄弟情谊是最好的。”几天前我去看他的时候,莫门用一种讽刺的语气对我说。
由于以色列无限的创造力,他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杀死我们——炸弹、四轴飞行器、被折磨致死、狙击手、疾病……随你挑!即使是加沙的流浪狗也应该感谢以色列无尽的食物——无数加沙人的尸体被埋在废墟下。
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我一直在经历的两难境地,在爱尔兰和加沙之间,在这里的和平与安全与那里的种族灭绝之间徘徊。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的梦想已经沦为希望有一个体面的坟墓,而不是成为流浪狗的一顿饭。
当以色列下令将加沙北部的120万居民疏散到南部时,我的堂兄艾哈迈德(Ahmed)拒绝离开自己的家,担心再次发生灾难(Nakba)。由于北方的饥荒,艾哈迈德的妻子、三个孩子和他的父母不得不撤离到南方,但他留下来了。在分开七个月后,去年五月,他得了肝炎。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情况下,他因极度饥饿而死于病毒。
艾哈迈德和我的年龄和名字都一样。我们一起长大。当我打电话给我的姑姑,艾哈迈德的母亲伊塔夫,表达我衷心的哀悼时,她念到我的名字时哭得很伤心。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和她说过话,因为我不想让她记住她的损失。
回到我在爱尔兰的生活,我喝了一口已经凉了的咖啡,强迫自己继续写论文,假装生活可以正常。但这一切都不正常,而且永远不会正常——只要以色列继续蓄意消灭加沙的所有人。
Ahmed Alsammak是一名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记者。他目前在都柏林攻读MBA。他是“我们不是数字”(We Are Not Numbers)的项目助理,这是一个在加沙地带由青年领导的巴勒斯坦非营利项目。Twitter: @Ahmed_al_sammak。
为您推荐:
- 我们的加沙地狱:“你所有的表亲都在家里,但他们现在被埋在废墟下” 2024-12-02
- 购买或赠送Babbel订阅,以74%的折扣学习一门新语言 2024-12-02
- 您现在可以在网上与ChatGPT的高级语音模式交谈 2024-12-02
- 兰德曼在烂番茄上的首个得分——它能延续泰勒·谢里丹的连胜吗? 2024-12-02
- 微软的新款迷你个人电脑是为办公室设计的这是它能做的 2024-12-02
- 苹果的粉丝们会喜欢Nomad的这款时尚的三合一充电器,现在它的售价为45美元 2024-12-02